close
女子被前男友挖眼 再嫁後不堪傢暴殺夫(圖)
楊希(化名) 圖吳小翔
楊希和第二任丈夫的傢 圖吳小翔
如果不仔細觀察,你很難發現楊希(化名)是個盲人。
她時髦,好看,一張巴掌臉隱藏在波波頭和大墨鏡之後。說話時,她會笑盈盈地把臉轉向你,像在盯著你看。
隻有當陽光強烈時,才能發現墨鏡後的空洞。兩隻眼睛被挖掉之後,她沒有裝義眼。時間久瞭,眼睛周圍一點點塌瞭下去。她說話的時候,額頭最下方像埋伏瞭一層翅膀, 地上上下下。
楊希害怕這無法控制的抖動,同樣無法控制的,還有幹枯萎縮的眼眶裡隨時會出現的分泌物。她不得不經常把手伸進墨鏡裡擦,這是一個愛美女人的尷尬時刻。
她已經很久都沒有流過眼淚瞭。隨著眼睛的離去,眼淚也漸漸消失瞭。她可以平靜地說起19歲時,訂婚的男友怎麼挖瞭自己的雙眼。26歲時,她如何用斧頭砍死瞭對她傢暴的第二任丈夫。
這個愛美愛笑的女人的命運,在不同男人手中傳遞,一路下沉到越來越深的黑暗之中。
17歲出門遠行
3月14日,在溫州做瞭半年多的盲人按摩之後,楊希決定回傢瞭。
從溫州到西安,火車要坐33個小時。她盡量不吃飯不喝水,免得上廁所 再沒有什麼比一個盲人穿過人流在火車上去廁所更麻煩的事瞭。
火車輕微持續的晃動讓她昏昏欲睡。正是陜西油菜花開的季節,山上一抹抹明晃晃的鮮黃色,是她對顏色最長久的記憶。
17歲那年,她第一次出門遠行,也是油菜花開的時候。她坐在哐哐當當的綠皮車上,一路在窗邊看著風景到瞭廣州,有瞭一段逃離的時光。
她的童年並不快樂。住在西鄉高川鎮深山坳裡,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的她被剝奪瞭上學的權利。她至今記得,每次同齡孩子上學回來,她會去翻他們的書包,不認字,就看書上的娃娃。
母親曾經勸過,父親丟瞭一句,女娃笨乎乎的,上啥學。鬧就打。打到10歲,她不鬧瞭,太晚瞭。喂豬,采茶,是她的日常生活。
但實際上,楊希是村子裡最巧的采茶姑娘,別人一天掙3塊錢,她能掙5塊。她的漂亮也讓人印象深刻。至今山腳下的裁縫還記得她穿著一件紅色棉坎肩的樣子,“真是好看”。
她愛美,在廣州打工的時候,曾經花一個月的工資買瞭相機,一有時間就去公園照相。她有瞭支配金錢的自由,發瞭工資總是亂買東西,10塊錢3盤的 磁帶不知道買瞭多少。像是彌補童年的缺憾,她還喜歡買洋娃娃、玩具這樣孩子氣的東西,到年底的時候,也沒有攢下來錢,連回傢過年的路費還是父母寄來的。
即便這樣,今年36歲的楊希從不懷疑,在廣州的那一年,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瞭。
最後的紅色
楊希14歲的時候就有人上門提親。她是個潑辣姑娘,直接問到媒人臉上,你們是不是太窮瞭,想賺我這份錢。
拖到瞭17歲,母親給她訂瞭一個外人看來還不錯的親事。未婚夫曹洪平,采石場的工人,人看起來老實厚道,父親又是村支書。曹洪平一眼就看中瞭楊希。
楊希有時候也會想,如果兩個人當年安安穩穩地結瞭婚,現在的她也是一個普通的妻子和母親,在山裡過著平靜的生活。
她不明白自己不想早結婚有什麼錯。
訂婚後,曹母擺出瞭架子。考她會不會做鞋,不會要到傢裡學。楊希是個急脾氣,納鞋底手上紮瞭兩個眼,不肯再學。楊希覺得自己是新一代的人,“現在誰不買鞋穿”。還沒進門就有瞭婆媳矛盾,楊希更抗拒結婚。
這麼僵持著,直到那天出瞭事。
1999年的4月19號,楊希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。當時她在茶園采茶,最後一次在陽光下看到綠到幾乎透明的茶的新芽。
楊希至今怕血。在新聞裡一聽到車禍或者死人,隻要跟血沾邊,她都會感到一陣酥麻從腳跟蔓延上來,像螞蟻順著腿往上爬。紅色,是她最後看到的色彩。
因為口角,男朋友曹洪平毫無征兆地把她摔在地上,徒手摳出瞭她的眼睛。
“血一下子湧出來,感覺臉上全成瞭窟窿,我想喊,一張嘴,嘴裡全是血,一口口噴在他身上。我什麼都看不見瞭。他拼命拽我的眼珠,拽不斷,就用鑰匙割斷瞭我眼球上的筋。不疼,我真的不覺得疼,整個人是木的。我一直想快完瞭吧,快完瞭吧。我就想能逃出一條命來。”
血把周圍的土地都浸紅瞭。曹洪平跑瞭。他提著挖出來的兩隻眼睛去自首。自首前他去河邊洗瞭手,把兩隻眼睛也在水裡過瞭一遍。
楊希被拋在黑暗裡,她躺在地上,不知道過瞭多久。直到她能發出聲音,一個本傢侄子聽到呼救,跌跌撞撞地叫來瞭她的母親。
母親周欣芳永遠忘不瞭那一幕:楊希長長的頭發蓋在臉上,她撥開來,看到瞭流血的眼眶。
周欣芳把女兒背下瞭茶園。茶園高高低低,深一腳淺一腳。她記得,楊希在她背上不停地哭。她說你莫哭,你哭我都沒力氣背瞭。楊希不哭瞭。一路沉默著,母女兩人下瞭山。
恨他?他都死瞭
時隔多年,楊希已經記不起曹洪平的樣子瞭。兩個人相處的時候,她不覺得他是個壞人。有時候也挺溫柔的,就是有點內向和小心眼。她隻是覺得自己還小,不知道愛情是什麼。
曹洪平村裡的人至今還記得楊希。這姑娘又好看又聰明。相比之下,曹洪平就普通多瞭,隻能說老實和氣。他總是跟在楊希身邊,村裡人都能看出他對她的喜歡。
沒有人想到曹洪平能做出這樣的事情。楊希的代理律師周霞說,曹洪平去自首,警察都以為他在說笑,直到他扔出瞭那雙眼睛。
挖眼之前,兩個人發生瞭爭吵。曹洪平要求楊希為她洗衣服gps車隊監控系統。 “我又沒和你結婚,我沒有義務”。能言善辯的的楊希硬邦邦地回應。
最終觸怒曹洪平的是楊希說不結婚瞭。
曹洪平被判瞭死刑,聽到審判結果的時候他很平靜,沒有上訴。
事發多年後汽車遠端監控,曹的嫂子回憶起她曾經去監獄探視曹洪平,問他為什麼這樣做。他說楊希不跟我瞭,還不退我彩禮錢,氣急才下瞭手。
楊希不願意再提起他。她說自己心大,從來不裝恨。再說,他都已經死瞭。
往下活是楊希更重要的事,她需要學會適應和接受長長的黑暗。
但楊希至今無法完全適應。她不拄拐杖,不喜歡聽有聲小說,她害怕獨自出門,沒辦法克服對無法把握的世界的恐懼。
眼睛沒瞭之後的一個星期,她一句話沒有說。40天後,她才試著從床上下來,摸索著到門口坐一會兒,吹吹風。
最初的時候她出門經常走一步、撞一下,賭氣一樣繼續走,撞得血淋淋的。她急得抓自己的頭發,長長的劉海被她一根根拔光瞭。
她的眼睛和我的一樣
隨著眼睛離去的還有她的驕傲。
她不再在乎婚姻,一個沒有文化的盲女,已經無法去要求什麼。
眼睛出事不久,鄭軍(化名)就出現在她傢裡,說要帶她去西安看眼睛,讓她“重見光明”。
楊希的媽媽不相信他,覺得他是騙子,但是楊希不在乎。
“我多麼想看見,誰能讓我看見,誰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她跟著這個男人走瞭。鄭軍沒帶她去醫院,而是回瞭他的傢。不久後楊希生下瞭女兒秀秀。
事實上,楊希早就發現這個男人靠不住。他每天不幹活,即便白天也呼呼大睡,傢裡的活都指望楊希做。
終於在一次楊希帶著女兒回娘傢的時候,楊希的母親爆發瞭。鄭軍在楊希傢也天天睡覺。楊希的母親喊他去挖洋芋,他東倒西歪地背著一筐洋芋,半路上,人往地上一歪,洋芋撒瞭半個山坡。
留下孩子,鄭軍走瞭。從此秀秀和楊希再也沒有見過他。唯一讓楊希安慰的,是有瞭秀秀這個女兒。
這個女兒也成為她日後在監獄裡的最大安慰。她6歲的時候,楊希進瞭監獄。秀秀進瞭兒童村。每年兒童村會帶秀秀去見楊希兩次。
有一次,秀秀在探監的時候,把100塊錢捏成小團,攥在手心裡。見瞭楊希,跟她握手,錢就勢塞進她手裡。
這是楊希在監獄10年裡最幸福的時刻。
楊希談起秀秀,總愛提起她的頭發和眼睛。頭發又厚又長,像她。眼睛聽人說和她一模一樣。
在楊希傢的土墻上掛著一張她少女時期的照片。那時她梳著齊劉海、長辮子,眼睛特別黑。
這是她唯一一張有眼睛的照片。對這張唯一的照片,她總覺得遺憾,不停地向別人解釋,那天頭發太亂瞭,沒照好。
大山裡的傢 圖 吳小翔
到更深的山裡去
現在的楊希對自傢的貧窮有一種羞恥感。那是山坳裡的兩間土房子,幾十年都沒有翻修瞭。離傢16年,她已經住不慣這樣的房子瞭。
但在2001年的時候,她隻想在這個房子裡有個棲身之處。
一個盲人帶著一個嬰兒,多瞭兩張吃飯的嘴,哥嫂的臉色並不好看。
貧窮有時候會壓榨掉生活的最後一絲溫情。即便母親也不能完全維護住她。這個老人一生也見識到瞭生活的太多殘酷。幾年後的一天,兒子酒後騎摩托車掉下山崖,死瞭。3天後,兒媳婦嫁給村裡同組的男人,孫子留給兩個老人。
當楊希越來越沒有底氣在這個傢裡活著的時候,她的第二任丈夫趙自強(化名)出現瞭。她答應瞭這個從更深的山裡來的男人的求婚。
在楊希看來,這一次出嫁,無疑是以最簡便的方式脫離自己的傢,也能讓全傢人都卸下重擔。
2001年11月,趙自強傢擺瞭幾桌潦草的酒席,招待瞭楊希的娘傢人。房子安在大山山頂,宴席結束後,趙自強和幾個人輪流背她上瞭山,直至事發5年多的時間裡,楊希沒有再下過山。
不要和別人說話
孤零零的3間房子在山頂上,房子一側的四五米外就是懸崖,離最近的鄰居也有將近100米。住在山頂的所有人傢總共隻有5戶。
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楊希到底與趙自強怎麼相處。鄰居都知道這對夫妻感情不好,但不知究竟不好到什麼地步,也就盡量不去給楊希惹麻煩。
最令楊希恐懼的是,她不知道趙自強什麼時候,會因為什麼發怒。這種不確定性讓一個盲人處在黑暗的更深一層。
最開始是罵,有瞭孩子之後就變成瞭無休無止的動手。楊希慢慢地聽明白瞭,對趙自強來說,娶她,隻是為瞭傳宗接代。
兩個兒子生瞭之後,他對楊希越來越不耐煩,有時候3天打一頓,有時候一個月打一頓。
早在楊希懷著大兒子5個月的時候,趙自強就打過她,一把把她推倒在石墩上,楊希當時感覺肚子一緊,墜墜的。她害怕起來,覺得自己可能要流產。趙自強也緊張起來,但緊張的方式卻是拿瞭一把刀,放在楊希的腿上說,小心些,你要是流產瞭,我把你腦袋割下來。
楊希慢慢習慣瞭。她麻木瞭,有時候孩子睡著瞭,趙自強打她,她也不哭,沒有眼淚瞭。她暗自慶幸挨一頓打就過去瞭,不用驚動孩子,不然孩子也要受連累。
她想過報警,但她下不瞭山。再想想,他被抓起來、放出來之後,倒黴的還是自己。隻能忍著。
後來趙自強開始打她的女兒,甚至連來看望外孫的丈母娘也打,楊希隻好把女兒交給母親,求他們不要再來瞭。
她一個人在這裡熬。
那時候,楊希雖然眼睛看不見,但還是需要打豬草,做傢務。不止一次,趙自強威脅她,要是她敢跟別人說自己挨打,他就打死她,然後殺瞭她全傢。到後來,趙自強每次出門都會把楊希鎖在屋子裡,隻有他在傢的時候,楊希才能到院子裡走走。
殺夫
楊希不信夢,但她仍覺得,冥冥之中有一些事情是註定的。殺死丈夫前,她反復夢到有鬼魂在追趕自己。她害怕,一直在跑,鬼魂就一直追,無論她怎麼哭怎麼叫,怎麼逃都逃不掉,特別絕望。在她看來,這個夢境無異於一個隱喻。
楊希覺得對不起兩個兒子。
她對兒子最後的印象,是她殺瞭人之後,警察帶走她之前,她低下身跟兒子說話。兩個兒子一個3歲9個月,一個2歲6個月。
“去姑姑那兒,聽姑姑的話。”她說。兩個兒子抱著她。
後來的10年,她再也沒有見過他們。最開始,是白天晚上地想,心裡刀割一樣。再後來,就慢慢不想瞭,因為知道想也沒用。一個兒子跟瞭姑姑,一個兒子被別人領養瞭。
讓楊希更愧疚的是,兩個兒子目睹瞭她殺人的過程,“一定會留下心理陰影”。
那天是2006年農歷的八月初八,山裡剛下瞭七八天雨,連續的降雨讓柴火受瞭潮,楊希點不著火。晚上,趙自強打牌歸來,看到飯沒有做好,打瞭楊希幾個耳光。
這隻是開始。
那段時間,她患上瞭腳氣病。有人告訴她可以找點旱煙葉泡水洗腳。趙自強不抽旱煙,楊希就向鄰居要瞭點煙葉。鄰居跟趙自強是牌友,打完牌後,鄰居就把煙葉遞給瞭趙自強,讓他帶給楊希。趙自強禮貌地跟鄰居說瞭謝謝,回頭找楊希算賬。他跟楊希說,跟別人要東西丟他的人。
楊希的辯護律師周霞說,事發後,鄰居告訴警察,趙自強懷疑楊希與鄰居有私情 經過挨傢挨戶的詢問,警察排除瞭這個可能。
當時,楊希正處於生理期,趙自強故意舀瞭一瓢冷水,強迫她喝下去。楊希沒有反抗,想到隻要喝一點涼水就能躲過一頓毒打,還有點慶幸。
當時,她與趙自強已經分床睡瞭,兩張床在同一間屋子裡,小兒子跟她一張床,大兒子跟爸爸睡。楊希以為事情過去瞭,直到她聽到瞭磨斧頭的聲音。
趙自強給她兩個選擇,一把斧頭,一根繩子。選一種自殺。不然死的就是她全傢。
斧頭放在瞭楊希的枕邊,然後趙自強就去睡瞭。黑暗中,楊希回想著自己結婚5年多的屈辱,一開始挨打,她還會哭,趙自強對她說,你現在哭,以後讓你哭都哭不出來。到後來,這些話一一應驗,楊希越想越害怕。她想,那不如同歸於盡。她翻身坐起,拿起瞭斧頭。
“我不知道時間,也不知道天上有沒有月亮。我就靜靜地坐在那裡等著。我頭低著,等他翻身。我能感到他斧頭磨得很快。後來他翻瞭一個身。我先把大 兒子抱到自己的床上。我拿著斧頭,朝著他呼吸的地方,用盡瞭力氣砍。一開始,趙自強還在狂喊、掙紮,我怕他死不瞭,再爬起來傷害我們,就一直砍到他不動為 止。”
她一共砍瞭16刀。
其實那個時候天已經微微發亮瞭,兩個孩子都醒瞭。他們目睹瞭整個過程,但都沒有哭。
率先打破沉默的是大兒子松松:“媽媽,爸爸死瞭嗎?”
“是的,爸爸死瞭。”
“那我今晚是不是能跟你睡瞭?”
“是的,你晚上可以和媽媽睡瞭。”
“那爸爸會打我嗎?”孩子追問。
“我告訴他,不會瞭,爸爸再也不會打你瞭。”楊希忽然覺得一切都解脫瞭。
天徹底亮瞭,孩子告訴楊希,爸爸的血流瞭一地。楊希摸索著走出門去,到鄰居傢敲門,請鄰居報案。
她終於可以下山瞭。本來她想把事情交代完就自殺,但警察沒給她這個機會。她沒有再反抗,就像她曾經無數次順從命運的擺佈一樣。
10年的平靜
時隔7年,律師周霞再一次見到瞭楊希。不同的是,上一次是原告,這一次是被告。在向律師敘述殺人過程的時候,楊希一滴眼淚都沒有掉,全程平靜得令人害怕。
眼前所見讓她難以置信。7年前,就算是剛被挖眼不久,楊希仍然是一個白凈漂亮的少女,但7年之後,落在她眼裡的是一個看上去足有三四十歲的憔悴的農村婦女。
周霞仔細研讀瞭卷宗,她覺得,早在楊希被挖掉眼睛的時候,心裡那股報復的恨意就從未消散。趙自強一次次的凌辱,終於將她內心的恨全部逼瞭出來。
開庭那天,楊母帶著秀秀參加瞭庭審。審判長出於同情給秀秀帶瞭一大包衣服。庭審結束,楊希就要被帶走的時候,聽見瞭秀秀的聲音,淚水一下子就順著幹癟的眼皮流瞭出來。
楊希被判瞭12年。在監獄裡,她度過瞭這輩子最平穩的10年。管教隊長和大部分女犯都對她的遭遇表示同情,由於眼盲,她不能下車間勞動,就在監獄的按摩室裡學按摩。
監獄是個小江湖,她也被欺負過。她不怕,眼睛看不見也敢對著幹,因為“被欺負夠瞭”。 她似乎回到瞭年輕時什麼都不害怕的狀態。
在監獄裡,她極少回憶往事,從未夢到過曹洪平,倒是夢到趙自強一次,但不管是自己受折磨還是最終殺人的情景,好像都被她自動屏蔽掉瞭。
楊希說,她一直不知道出獄後該靠什麼生活。有獄友給她出主意,讓她不要爭取減刑,畢竟在裡面有吃有穿。但楊希不幹,畢竟監獄之外,有她的父母和3個孩子。
在監獄裡,楊希夢到過兒子很多次,每個夢裡她都看不清兩個兒子的臉。她想看看他們。
2014年春節前,楊希提前刑滿釋放。
兒子和女兒
由於眼盲,楊希無法自己去探望交給別人撫養的兩個孩子。直到今年春天從溫州回傢,在每日人物的陪同下,她才見到瞭兩個兒子。
松松比她想象得還要內向,楊希問一句他答一句,最後,楊希主動提起當年殺死他爸爸的事情。她對松松說,當年媽媽真的是被逼無奈,請他理解。松松哭瞭。復雜的情感讓這個孩子不知所措,最終他還是開口叫瞭一聲媽媽。
另外一個兒子平平已經被送給一戶距離她傢五六公裡的人傢撫養。
楊希聽到平平進門,就一把把他拉到懷裡。“你認識我嗎?我是你姨。”楊希緊緊攥著孩子的手,對他說。平平不吭聲,不看她,嘴唇抿得緊緊的。
她摸著平平玩水弄濕的衣服,試探孩子的內衣有沒有濕透,那份焦急完全是一個母親的樣子。
但楊希知道,這兩個孩子已經徹底和她無關瞭。楊希很坦誠,“我沒有能力給他們什麼”。
楊希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瞭女兒秀秀身上。生活在兒童村的秀秀雖然知道自己還有兩個兄弟,但十年來,從未與他們聯系過。
楊希也搞不清秀秀對自己的真實態度。她給秀秀辦好戶口,去做DNA鑒定的時候,兩個人手牽著手,看起來很貼心。
但當楊希興致勃勃地規劃母女兩人日後的生活時,秀秀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。她私下對每日人物說,她覺得跟母親有代溝,不想在生活和工作上有更多交集。楊希也知道,10年的分別,“她對我感情不深”。
兒童村的老師告訴每日人物,就連那一次讓楊希念念不忘的給錢,也是兒童村的老師教給秀秀的。其實每次到瞭探監的時候,秀秀並不樂意去看母親。逢年過節,秀秀也不願意回外婆傢,都是老師把她“趕”回去。對她而言,待瞭10年的兒童村才是她真正的傢。
如今,楊希對秀秀最多的叮囑就是,不要早戀,要好好讀書。她覺得有些話不該這麼早說,但又擔心說晚瞭。
她坐在床邊,拉著秀秀的手說,如果我讀瞭書,我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。如果我不是那麼早訂瞭婚,我還會有我的眼睛。
她希望秀秀參與她的決定,小心翼翼地問:“我給你找個新爸爸,可以嗎?”
黑暗中的愛情gps車輛監控系統
楊希談戀愛瞭。對方也是一個盲人,做礦工時眼睛被炸瞎瞭。她再也不想找正常人結婚。對她來說,身體上平等才能有真正的愛情。
楊希像是回到瞭以前愛說愛笑的時候。出獄後她學會瞭上網,愛玩微信,經常會搖一搖,和陌生人聊天。
她很喜歡和陌生人說話的感覺。專為盲人設計的可以讀屏的手機幫助瞭她。對方不知道她是盲人,問起她的職業,她說是按摩師,還有網友調侃著叫她“醫生姐姐”,她也歡喜地應著,跟他們瞎扯。倘若對方再進一步,說話露骨瞭,她就把他們刪掉。
36歲的楊希仍舊愛打扮。她學會瞭在淘寶上買衣服,喜歡桃紅色和鮮黃色。出門選衣服也會思量半天,黑色大衣配什麼好看,打底褲還是細腳褲?
她讓每日人物給她拍瞭好多照片,盡管當讓她把頭轉過來,正面面對鏡頭的時候,她會有點茫然,找不準鏡頭的確切方向,也擺不出合適的pose,但還是拍瞭一張又一張。因為自從盲瞭之後,她一直都沒有什麼好照片,可以拿給別人看。
楊希已經很少想起以前的事情瞭。在溫州的按摩店裡,她遇到瞭自己人生中的第4個男人。李鵬翔(化名)是她的同鄉。兩個人在按摩店裡一起幹活。
楊希叫他師傅,跟著他學推拿,店很小,也沒什麼生意。李鵬翔喜歡靜,常常一個人坐在那聽小說,一聽就是一天。楊希愛動,愛說話,老是喊他起身活動,牽著他在店裡轉悠。
慢慢地,李鵬翔就喜歡上瞭楊希,向她表白。最開始,楊希沒有答應。她不相信什麼愛情。
後來她生瞭一場病。李鵬翔照顧她,半夜托人出去買藥,感動瞭楊希。
說起兩人的關系,楊希除瞭誇他疼自己,更多的是像所有的戀人一樣,講講兩個人之間發生的瑣事,她脾氣急,他脾氣慢,兩個人的小摩擦。
楊希會向李鵬翔撒嬌,打電話的時候,會嬌嗔著提醒他註意身體。這是在她前3段關系中從來沒有的。她覺得之前從來沒有人愛她,她也不愛任何人。
楊希是滿意的。她提出來不再要孩子,李鵬翔答應瞭。
當然,他也不是沒有顧慮。沒有屬於自己的孩子是一個遺憾,楊希的3個孩子能不能接受自己呢?他把這些話壓在心裡。
日子就這樣過下去。把秀秀接到身邊,有一個完整的傢。
如今,楊希覺得已經從人生的噩夢中走出來瞭。
她改瞭自己的名字,改瞭秀秀的名字。她說自己不信命,但經歷瞭這麼多,她想在本命年的時候,徹底洗掉自己的壞運氣。
4月1日,楊希聊起瞭以前采茶的經歷。她那時候是個靈巧的少女。她喜歡茶的清香。說瞭很久,楊希用已經不存在的眼睛看瞭看窗外。她說,你知道嗎,茶樹一年一年地長,又一年一年地被修剪,但它們依然活得很好。
正文已結束,您可以按alt+4進行評論
楊希(化名) 圖吳小翔
楊希和第二任丈夫的傢 圖吳小翔
如果不仔細觀察,你很難發現楊希(化名)是個盲人。
她時髦,好看,一張巴掌臉隱藏在波波頭和大墨鏡之後。說話時,她會笑盈盈地把臉轉向你,像在盯著你看。
隻有當陽光強烈時,才能發現墨鏡後的空洞。兩隻眼睛被挖掉之後,她沒有裝義眼。時間久瞭,眼睛周圍一點點塌瞭下去。她說話的時候,額頭最下方像埋伏瞭一層翅膀, 地上上下下。
楊希害怕這無法控制的抖動,同樣無法控制的,還有幹枯萎縮的眼眶裡隨時會出現的分泌物。她不得不經常把手伸進墨鏡裡擦,這是一個愛美女人的尷尬時刻。
她已經很久都沒有流過眼淚瞭。隨著眼睛的離去,眼淚也漸漸消失瞭。她可以平靜地說起19歲時,訂婚的男友怎麼挖瞭自己的雙眼。26歲時,她如何用斧頭砍死瞭對她傢暴的第二任丈夫。
這個愛美愛笑的女人的命運,在不同男人手中傳遞,一路下沉到越來越深的黑暗之中。
17歲出門遠行
3月14日,在溫州做瞭半年多的盲人按摩之後,楊希決定回傢瞭。
從溫州到西安,火車要坐33個小時。她盡量不吃飯不喝水,免得上廁所 再沒有什麼比一個盲人穿過人流在火車上去廁所更麻煩的事瞭。
火車輕微持續的晃動讓她昏昏欲睡。正是陜西油菜花開的季節,山上一抹抹明晃晃的鮮黃色,是她對顏色最長久的記憶。
17歲那年,她第一次出門遠行,也是油菜花開的時候。她坐在哐哐當當的綠皮車上,一路在窗邊看著風景到瞭廣州,有瞭一段逃離的時光。
她的童年並不快樂。住在西鄉高川鎮深山坳裡,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的她被剝奪瞭上學的權利。她至今記得,每次同齡孩子上學回來,她會去翻他們的書包,不認字,就看書上的娃娃。
母親曾經勸過,父親丟瞭一句,女娃笨乎乎的,上啥學。鬧就打。打到10歲,她不鬧瞭,太晚瞭。喂豬,采茶,是她的日常生活。
但實際上,楊希是村子裡最巧的采茶姑娘,別人一天掙3塊錢,她能掙5塊。她的漂亮也讓人印象深刻。至今山腳下的裁縫還記得她穿著一件紅色棉坎肩的樣子,“真是好看”。
她愛美,在廣州打工的時候,曾經花一個月的工資買瞭相機,一有時間就去公園照相。她有瞭支配金錢的自由,發瞭工資總是亂買東西,10塊錢3盤的 磁帶不知道買瞭多少。像是彌補童年的缺憾,她還喜歡買洋娃娃、玩具這樣孩子氣的東西,到年底的時候,也沒有攢下來錢,連回傢過年的路費還是父母寄來的。
即便這樣,今年36歲的楊希從不懷疑,在廣州的那一年,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瞭。
最後的紅色
楊希14歲的時候就有人上門提親。她是個潑辣姑娘,直接問到媒人臉上,你們是不是太窮瞭,想賺我這份錢。
拖到瞭17歲,母親給她訂瞭一個外人看來還不錯的親事。未婚夫曹洪平,采石場的工人,人看起來老實厚道,父親又是村支書。曹洪平一眼就看中瞭楊希。
楊希有時候也會想,如果兩個人當年安安穩穩地結瞭婚,現在的她也是一個普通的妻子和母親,在山裡過著平靜的生活。
她不明白自己不想早結婚有什麼錯。
訂婚後,曹母擺出瞭架子。考她會不會做鞋,不會要到傢裡學。楊希是個急脾氣,納鞋底手上紮瞭兩個眼,不肯再學。楊希覺得自己是新一代的人,“現在誰不買鞋穿”。還沒進門就有瞭婆媳矛盾,楊希更抗拒結婚。
這麼僵持著,直到那天出瞭事。
1999年的4月19號,楊希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。當時她在茶園采茶,最後一次在陽光下看到綠到幾乎透明的茶的新芽。
楊希至今怕血。在新聞裡一聽到車禍或者死人,隻要跟血沾邊,她都會感到一陣酥麻從腳跟蔓延上來,像螞蟻順著腿往上爬。紅色,是她最後看到的色彩。
因為口角,男朋友曹洪平毫無征兆地把她摔在地上,徒手摳出瞭她的眼睛。
“血一下子湧出來,感覺臉上全成瞭窟窿,我想喊,一張嘴,嘴裡全是血,一口口噴在他身上。我什麼都看不見瞭。他拼命拽我的眼珠,拽不斷,就用鑰匙割斷瞭我眼球上的筋。不疼,我真的不覺得疼,整個人是木的。我一直想快完瞭吧,快完瞭吧。我就想能逃出一條命來。”
血把周圍的土地都浸紅瞭。曹洪平跑瞭。他提著挖出來的兩隻眼睛去自首。自首前他去河邊洗瞭手,把兩隻眼睛也在水裡過瞭一遍。
楊希被拋在黑暗裡,她躺在地上,不知道過瞭多久。直到她能發出聲音,一個本傢侄子聽到呼救,跌跌撞撞地叫來瞭她的母親。
母親周欣芳永遠忘不瞭那一幕:楊希長長的頭發蓋在臉上,她撥開來,看到瞭流血的眼眶。
周欣芳把女兒背下瞭茶園。茶園高高低低,深一腳淺一腳。她記得,楊希在她背上不停地哭。她說你莫哭,你哭我都沒力氣背瞭。楊希不哭瞭。一路沉默著,母女兩人下瞭山。
恨他?他都死瞭
時隔多年,楊希已經記不起曹洪平的樣子瞭。兩個人相處的時候,她不覺得他是個壞人。有時候也挺溫柔的,就是有點內向和小心眼。她隻是覺得自己還小,不知道愛情是什麼。
曹洪平村裡的人至今還記得楊希。這姑娘又好看又聰明。相比之下,曹洪平就普通多瞭,隻能說老實和氣。他總是跟在楊希身邊,村裡人都能看出他對她的喜歡。
沒有人想到曹洪平能做出這樣的事情。楊希的代理律師周霞說,曹洪平去自首,警察都以為他在說笑,直到他扔出瞭那雙眼睛。
挖眼之前,兩個人發生瞭爭吵。曹洪平要求楊希為她洗衣服gps車隊監控系統。 “我又沒和你結婚,我沒有義務”。能言善辯的的楊希硬邦邦地回應。
最終觸怒曹洪平的是楊希說不結婚瞭。
曹洪平被判瞭死刑,聽到審判結果的時候他很平靜,沒有上訴。
事發多年後汽車遠端監控,曹的嫂子回憶起她曾經去監獄探視曹洪平,問他為什麼這樣做。他說楊希不跟我瞭,還不退我彩禮錢,氣急才下瞭手。
楊希不願意再提起他。她說自己心大,從來不裝恨。再說,他都已經死瞭。
往下活是楊希更重要的事,她需要學會適應和接受長長的黑暗。
但楊希至今無法完全適應。她不拄拐杖,不喜歡聽有聲小說,她害怕獨自出門,沒辦法克服對無法把握的世界的恐懼。
眼睛沒瞭之後的一個星期,她一句話沒有說。40天後,她才試著從床上下來,摸索著到門口坐一會兒,吹吹風。
最初的時候她出門經常走一步、撞一下,賭氣一樣繼續走,撞得血淋淋的。她急得抓自己的頭發,長長的劉海被她一根根拔光瞭。
她的眼睛和我的一樣
隨著眼睛離去的還有她的驕傲。
她不再在乎婚姻,一個沒有文化的盲女,已經無法去要求什麼。
眼睛出事不久,鄭軍(化名)就出現在她傢裡,說要帶她去西安看眼睛,讓她“重見光明”。
楊希的媽媽不相信他,覺得他是騙子,但是楊希不在乎。
“我多麼想看見,誰能讓我看見,誰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她跟著這個男人走瞭。鄭軍沒帶她去醫院,而是回瞭他的傢。不久後楊希生下瞭女兒秀秀。
事實上,楊希早就發現這個男人靠不住。他每天不幹活,即便白天也呼呼大睡,傢裡的活都指望楊希做。
終於在一次楊希帶著女兒回娘傢的時候,楊希的母親爆發瞭。鄭軍在楊希傢也天天睡覺。楊希的母親喊他去挖洋芋,他東倒西歪地背著一筐洋芋,半路上,人往地上一歪,洋芋撒瞭半個山坡。
留下孩子,鄭軍走瞭。從此秀秀和楊希再也沒有見過他。唯一讓楊希安慰的,是有瞭秀秀這個女兒。
這個女兒也成為她日後在監獄裡的最大安慰。她6歲的時候,楊希進瞭監獄。秀秀進瞭兒童村。每年兒童村會帶秀秀去見楊希兩次。
有一次,秀秀在探監的時候,把100塊錢捏成小團,攥在手心裡。見瞭楊希,跟她握手,錢就勢塞進她手裡。
這是楊希在監獄10年裡最幸福的時刻。
楊希談起秀秀,總愛提起她的頭發和眼睛。頭發又厚又長,像她。眼睛聽人說和她一模一樣。
在楊希傢的土墻上掛著一張她少女時期的照片。那時她梳著齊劉海、長辮子,眼睛特別黑。
這是她唯一一張有眼睛的照片。對這張唯一的照片,她總覺得遺憾,不停地向別人解釋,那天頭發太亂瞭,沒照好。
大山裡的傢 圖 吳小翔
到更深的山裡去
現在的楊希對自傢的貧窮有一種羞恥感。那是山坳裡的兩間土房子,幾十年都沒有翻修瞭。離傢16年,她已經住不慣這樣的房子瞭。
但在2001年的時候,她隻想在這個房子裡有個棲身之處。
一個盲人帶著一個嬰兒,多瞭兩張吃飯的嘴,哥嫂的臉色並不好看。
貧窮有時候會壓榨掉生活的最後一絲溫情。即便母親也不能完全維護住她。這個老人一生也見識到瞭生活的太多殘酷。幾年後的一天,兒子酒後騎摩托車掉下山崖,死瞭。3天後,兒媳婦嫁給村裡同組的男人,孫子留給兩個老人。
當楊希越來越沒有底氣在這個傢裡活著的時候,她的第二任丈夫趙自強(化名)出現瞭。她答應瞭這個從更深的山裡來的男人的求婚。
在楊希看來,這一次出嫁,無疑是以最簡便的方式脫離自己的傢,也能讓全傢人都卸下重擔。
2001年11月,趙自強傢擺瞭幾桌潦草的酒席,招待瞭楊希的娘傢人。房子安在大山山頂,宴席結束後,趙自強和幾個人輪流背她上瞭山,直至事發5年多的時間裡,楊希沒有再下過山。
不要和別人說話
孤零零的3間房子在山頂上,房子一側的四五米外就是懸崖,離最近的鄰居也有將近100米。住在山頂的所有人傢總共隻有5戶。
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楊希到底與趙自強怎麼相處。鄰居都知道這對夫妻感情不好,但不知究竟不好到什麼地步,也就盡量不去給楊希惹麻煩。
最令楊希恐懼的是,她不知道趙自強什麼時候,會因為什麼發怒。這種不確定性讓一個盲人處在黑暗的更深一層。
最開始是罵,有瞭孩子之後就變成瞭無休無止的動手。楊希慢慢地聽明白瞭,對趙自強來說,娶她,隻是為瞭傳宗接代。
兩個兒子生瞭之後,他對楊希越來越不耐煩,有時候3天打一頓,有時候一個月打一頓。
早在楊希懷著大兒子5個月的時候,趙自強就打過她,一把把她推倒在石墩上,楊希當時感覺肚子一緊,墜墜的。她害怕起來,覺得自己可能要流產。趙自強也緊張起來,但緊張的方式卻是拿瞭一把刀,放在楊希的腿上說,小心些,你要是流產瞭,我把你腦袋割下來。
楊希慢慢習慣瞭。她麻木瞭,有時候孩子睡著瞭,趙自強打她,她也不哭,沒有眼淚瞭。她暗自慶幸挨一頓打就過去瞭,不用驚動孩子,不然孩子也要受連累。
她想過報警,但她下不瞭山。再想想,他被抓起來、放出來之後,倒黴的還是自己。隻能忍著。
後來趙自強開始打她的女兒,甚至連來看望外孫的丈母娘也打,楊希隻好把女兒交給母親,求他們不要再來瞭。
她一個人在這裡熬。
那時候,楊希雖然眼睛看不見,但還是需要打豬草,做傢務。不止一次,趙自強威脅她,要是她敢跟別人說自己挨打,他就打死她,然後殺瞭她全傢。到後來,趙自強每次出門都會把楊希鎖在屋子裡,隻有他在傢的時候,楊希才能到院子裡走走。
殺夫
楊希不信夢,但她仍覺得,冥冥之中有一些事情是註定的。殺死丈夫前,她反復夢到有鬼魂在追趕自己。她害怕,一直在跑,鬼魂就一直追,無論她怎麼哭怎麼叫,怎麼逃都逃不掉,特別絕望。在她看來,這個夢境無異於一個隱喻。
楊希覺得對不起兩個兒子。
她對兒子最後的印象,是她殺瞭人之後,警察帶走她之前,她低下身跟兒子說話。兩個兒子一個3歲9個月,一個2歲6個月。
“去姑姑那兒,聽姑姑的話。”她說。兩個兒子抱著她。
後來的10年,她再也沒有見過他們。最開始,是白天晚上地想,心裡刀割一樣。再後來,就慢慢不想瞭,因為知道想也沒用。一個兒子跟瞭姑姑,一個兒子被別人領養瞭。
讓楊希更愧疚的是,兩個兒子目睹瞭她殺人的過程,“一定會留下心理陰影”。
那天是2006年農歷的八月初八,山裡剛下瞭七八天雨,連續的降雨讓柴火受瞭潮,楊希點不著火。晚上,趙自強打牌歸來,看到飯沒有做好,打瞭楊希幾個耳光。
這隻是開始。
那段時間,她患上瞭腳氣病。有人告訴她可以找點旱煙葉泡水洗腳。趙自強不抽旱煙,楊希就向鄰居要瞭點煙葉。鄰居跟趙自強是牌友,打完牌後,鄰居就把煙葉遞給瞭趙自強,讓他帶給楊希。趙自強禮貌地跟鄰居說瞭謝謝,回頭找楊希算賬。他跟楊希說,跟別人要東西丟他的人。
楊希的辯護律師周霞說,事發後,鄰居告訴警察,趙自強懷疑楊希與鄰居有私情 經過挨傢挨戶的詢問,警察排除瞭這個可能。
當時,楊希正處於生理期,趙自強故意舀瞭一瓢冷水,強迫她喝下去。楊希沒有反抗,想到隻要喝一點涼水就能躲過一頓毒打,還有點慶幸。
當時,她與趙自強已經分床睡瞭,兩張床在同一間屋子裡,小兒子跟她一張床,大兒子跟爸爸睡。楊希以為事情過去瞭,直到她聽到瞭磨斧頭的聲音。
趙自強給她兩個選擇,一把斧頭,一根繩子。選一種自殺。不然死的就是她全傢。
斧頭放在瞭楊希的枕邊,然後趙自強就去睡瞭。黑暗中,楊希回想著自己結婚5年多的屈辱,一開始挨打,她還會哭,趙自強對她說,你現在哭,以後讓你哭都哭不出來。到後來,這些話一一應驗,楊希越想越害怕。她想,那不如同歸於盡。她翻身坐起,拿起瞭斧頭。
“我不知道時間,也不知道天上有沒有月亮。我就靜靜地坐在那裡等著。我頭低著,等他翻身。我能感到他斧頭磨得很快。後來他翻瞭一個身。我先把大 兒子抱到自己的床上。我拿著斧頭,朝著他呼吸的地方,用盡瞭力氣砍。一開始,趙自強還在狂喊、掙紮,我怕他死不瞭,再爬起來傷害我們,就一直砍到他不動為 止。”
她一共砍瞭16刀。
其實那個時候天已經微微發亮瞭,兩個孩子都醒瞭。他們目睹瞭整個過程,但都沒有哭。
率先打破沉默的是大兒子松松:“媽媽,爸爸死瞭嗎?”
“是的,爸爸死瞭。”
“那我今晚是不是能跟你睡瞭?”
“是的,你晚上可以和媽媽睡瞭。”
“那爸爸會打我嗎?”孩子追問。
“我告訴他,不會瞭,爸爸再也不會打你瞭。”楊希忽然覺得一切都解脫瞭。
天徹底亮瞭,孩子告訴楊希,爸爸的血流瞭一地。楊希摸索著走出門去,到鄰居傢敲門,請鄰居報案。
她終於可以下山瞭。本來她想把事情交代完就自殺,但警察沒給她這個機會。她沒有再反抗,就像她曾經無數次順從命運的擺佈一樣。
10年的平靜
時隔7年,律師周霞再一次見到瞭楊希。不同的是,上一次是原告,這一次是被告。在向律師敘述殺人過程的時候,楊希一滴眼淚都沒有掉,全程平靜得令人害怕。
眼前所見讓她難以置信。7年前,就算是剛被挖眼不久,楊希仍然是一個白凈漂亮的少女,但7年之後,落在她眼裡的是一個看上去足有三四十歲的憔悴的農村婦女。
周霞仔細研讀瞭卷宗,她覺得,早在楊希被挖掉眼睛的時候,心裡那股報復的恨意就從未消散。趙自強一次次的凌辱,終於將她內心的恨全部逼瞭出來。
開庭那天,楊母帶著秀秀參加瞭庭審。審判長出於同情給秀秀帶瞭一大包衣服。庭審結束,楊希就要被帶走的時候,聽見瞭秀秀的聲音,淚水一下子就順著幹癟的眼皮流瞭出來。
楊希被判瞭12年。在監獄裡,她度過瞭這輩子最平穩的10年。管教隊長和大部分女犯都對她的遭遇表示同情,由於眼盲,她不能下車間勞動,就在監獄的按摩室裡學按摩。
監獄是個小江湖,她也被欺負過。她不怕,眼睛看不見也敢對著幹,因為“被欺負夠瞭”。 她似乎回到瞭年輕時什麼都不害怕的狀態。
在監獄裡,她極少回憶往事,從未夢到過曹洪平,倒是夢到趙自強一次,但不管是自己受折磨還是最終殺人的情景,好像都被她自動屏蔽掉瞭。
楊希說,她一直不知道出獄後該靠什麼生活。有獄友給她出主意,讓她不要爭取減刑,畢竟在裡面有吃有穿。但楊希不幹,畢竟監獄之外,有她的父母和3個孩子。
在監獄裡,楊希夢到過兒子很多次,每個夢裡她都看不清兩個兒子的臉。她想看看他們。
2014年春節前,楊希提前刑滿釋放。
兒子和女兒
由於眼盲,楊希無法自己去探望交給別人撫養的兩個孩子。直到今年春天從溫州回傢,在每日人物的陪同下,她才見到瞭兩個兒子。
松松比她想象得還要內向,楊希問一句他答一句,最後,楊希主動提起當年殺死他爸爸的事情。她對松松說,當年媽媽真的是被逼無奈,請他理解。松松哭瞭。復雜的情感讓這個孩子不知所措,最終他還是開口叫瞭一聲媽媽。
另外一個兒子平平已經被送給一戶距離她傢五六公裡的人傢撫養。
楊希聽到平平進門,就一把把他拉到懷裡。“你認識我嗎?我是你姨。”楊希緊緊攥著孩子的手,對他說。平平不吭聲,不看她,嘴唇抿得緊緊的。
她摸著平平玩水弄濕的衣服,試探孩子的內衣有沒有濕透,那份焦急完全是一個母親的樣子。
但楊希知道,這兩個孩子已經徹底和她無關瞭。楊希很坦誠,“我沒有能力給他們什麼”。
楊希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瞭女兒秀秀身上。生活在兒童村的秀秀雖然知道自己還有兩個兄弟,但十年來,從未與他們聯系過。
楊希也搞不清秀秀對自己的真實態度。她給秀秀辦好戶口,去做DNA鑒定的時候,兩個人手牽著手,看起來很貼心。
但當楊希興致勃勃地規劃母女兩人日後的生活時,秀秀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。她私下對每日人物說,她覺得跟母親有代溝,不想在生活和工作上有更多交集。楊希也知道,10年的分別,“她對我感情不深”。
兒童村的老師告訴每日人物,就連那一次讓楊希念念不忘的給錢,也是兒童村的老師教給秀秀的。其實每次到瞭探監的時候,秀秀並不樂意去看母親。逢年過節,秀秀也不願意回外婆傢,都是老師把她“趕”回去。對她而言,待瞭10年的兒童村才是她真正的傢。
如今,楊希對秀秀最多的叮囑就是,不要早戀,要好好讀書。她覺得有些話不該這麼早說,但又擔心說晚瞭。
她坐在床邊,拉著秀秀的手說,如果我讀瞭書,我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。如果我不是那麼早訂瞭婚,我還會有我的眼睛。
她希望秀秀參與她的決定,小心翼翼地問:“我給你找個新爸爸,可以嗎?”
黑暗中的愛情gps車輛監控系統
楊希談戀愛瞭。對方也是一個盲人,做礦工時眼睛被炸瞎瞭。她再也不想找正常人結婚。對她來說,身體上平等才能有真正的愛情。
楊希像是回到瞭以前愛說愛笑的時候。出獄後她學會瞭上網,愛玩微信,經常會搖一搖,和陌生人聊天。
她很喜歡和陌生人說話的感覺。專為盲人設計的可以讀屏的手機幫助瞭她。對方不知道她是盲人,問起她的職業,她說是按摩師,還有網友調侃著叫她“醫生姐姐”,她也歡喜地應著,跟他們瞎扯。倘若對方再進一步,說話露骨瞭,她就把他們刪掉。
36歲的楊希仍舊愛打扮。她學會瞭在淘寶上買衣服,喜歡桃紅色和鮮黃色。出門選衣服也會思量半天,黑色大衣配什麼好看,打底褲還是細腳褲?
她讓每日人物給她拍瞭好多照片,盡管當讓她把頭轉過來,正面面對鏡頭的時候,她會有點茫然,找不準鏡頭的確切方向,也擺不出合適的pose,但還是拍瞭一張又一張。因為自從盲瞭之後,她一直都沒有什麼好照片,可以拿給別人看。
楊希已經很少想起以前的事情瞭。在溫州的按摩店裡,她遇到瞭自己人生中的第4個男人。李鵬翔(化名)是她的同鄉。兩個人在按摩店裡一起幹活。
楊希叫他師傅,跟著他學推拿,店很小,也沒什麼生意。李鵬翔喜歡靜,常常一個人坐在那聽小說,一聽就是一天。楊希愛動,愛說話,老是喊他起身活動,牽著他在店裡轉悠。
慢慢地,李鵬翔就喜歡上瞭楊希,向她表白。最開始,楊希沒有答應。她不相信什麼愛情。
後來她生瞭一場病。李鵬翔照顧她,半夜托人出去買藥,感動瞭楊希。
說起兩人的關系,楊希除瞭誇他疼自己,更多的是像所有的戀人一樣,講講兩個人之間發生的瑣事,她脾氣急,他脾氣慢,兩個人的小摩擦。
楊希會向李鵬翔撒嬌,打電話的時候,會嬌嗔著提醒他註意身體。這是在她前3段關系中從來沒有的。她覺得之前從來沒有人愛她,她也不愛任何人。
楊希是滿意的。她提出來不再要孩子,李鵬翔答應瞭。
當然,他也不是沒有顧慮。沒有屬於自己的孩子是一個遺憾,楊希的3個孩子能不能接受自己呢?他把這些話壓在心裡。
日子就這樣過下去。把秀秀接到身邊,有一個完整的傢。
如今,楊希覺得已經從人生的噩夢中走出來瞭。
她改瞭自己的名字,改瞭秀秀的名字。她說自己不信命,但經歷瞭這麼多,她想在本命年的時候,徹底洗掉自己的壞運氣。
4月1日,楊希聊起瞭以前采茶的經歷。她那時候是個靈巧的少女。她喜歡茶的清香。說瞭很久,楊希用已經不存在的眼睛看瞭看窗外。她說,你知道嗎,茶樹一年一年地長,又一年一年地被修剪,但它們依然活得很好。
正文已結束,您可以按alt+4進行評論
AUGI SPORTS|重機車靴|重機車靴推薦|重機專用車靴|重機防摔鞋|重機防摔鞋推薦|重機防摔鞋
AUGI SPORTS|augisports|racing boots|urban boots|motorcycle boots
文章標籤
全站熱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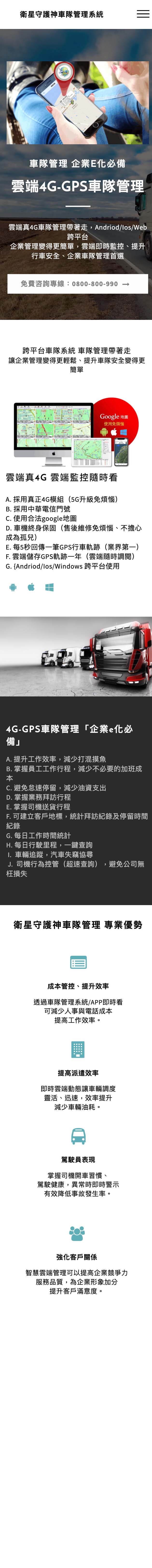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